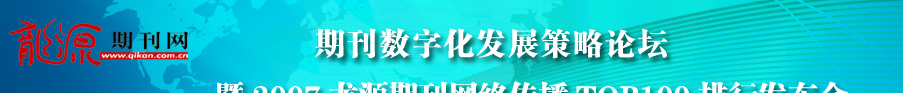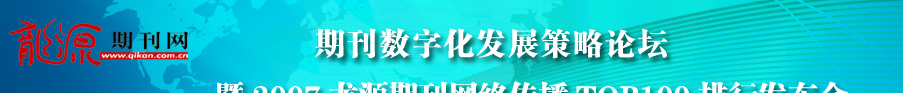|
| 刘旗辉 |
很高兴,首先感谢龙源期刊网给我们这次机会,演讲前先讲三个小感受。第一,前面的同志把我们的时间占得太多,我要提出抗议,给我们的机会太少,小小的抗议。另外一个,我觉得刚才李频讲得很好,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是怎么样的,我们需要自己动脑,因为现在我们得到的很多数据并不真实性,影响了我们的判断。还有一个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防止一种现象,自娱自乐。。
把自己干了20多年的期刊,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合讲,十几年来一个人埋在重庆,现在进军北京了,家也搬过来了,有很多办期刊的感受。我讲的标题是中国期刊业的未来猜想,因为我们不敢确定是什么东西,只能是一种猜想。
我觉得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期刊作为纸介文化产品将长期存在下去;第二个,中国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中国期刊的发展空间;第三个,我想简单地把我们《商界》的案例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最后一个就是要找到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是什么?期刊必须完成公司化、产品化的多元立体进程。
首先,我认为我们讨论了这么多问题,觉得数字化像老虎一样,像狼一样,但是我认为我们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比较模糊的,就是纸质期刊和数字期刊是两种不同的产品,我们这些产品是龙源期刊网的配套商,我们把我们的杂志办好,交给汤总他们,他们的整个产品就是龙源期刊的平台,他们去给我们发售,每年分钱给我们,这是两种不同的产品,我们不能把这两种不同的产品混为一谈。
另外我认为传统期刊的市场份额也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个市场份额是市场的需求决定的,所以很多期刊,以前我们也做,每个期刊去做网站,特别是我们《商界》,就像一个很大的门户网站,走不通,我认为这条路早晚是死路一条。我做期刊我就做期刊,我认为期刊和互联网最后只是一种互动,我后面也要讲。另外我认为新媒体只能提供人们对新闻和即时资讯满足,而非理性的文化产品,当然这个也应该值得讨论,因为我写这个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认为传统的期刊和新媒体在业态上有很多交叉,但是它们谁也代替不了谁,至少在相当的时间内,未来的路我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至少我看不到谁能够代替谁,只是我的一个体会,这些文字的东西大家可以看,我不多加阐述了。
这个问题就是,我认为中国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才仅仅开始,这个文化产品我认为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文化产品。从各个方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思想的进步,观念的转变,我认为对文化的产品的需求呈极强的上升趋势,这种东西我认为互联网不重,我们期刊也不重,我认为在这方面的作用,期刊可能还会发挥得更大一点,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文章,我认为很有道理,就是说人类的互联网长期这样下去会不会削弱人的理性思考,这是香港人发表的。我在海外的一个报纸上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的,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快餐、短俗、实用、现实,很多很多感性上的东西比较多,会不会未来长期的这样下去对我们人类的整个理性的思考是一个冲击?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大家可以思考,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认为,中国人均收入仍然很低,是世界上人均电脑占有率最低的过程,刚刚张社长谈了一下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事实上现在北京的互联网发展,北京的人均占有电脑率也很高,但是纸质的消费品,报纸,现在我看有时候早上稍微晚一点,京华时报这些都买不到,还有杂志,我给大家讲,当初我们《商界》到北京来,第一次有五百本运到北京,卖到了三百多本,我当时悲伤得不得了,当然现在上万了,北京这个地方纸质的期刊我认为应该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的。
还有一个,我认为中国的二元化结构突出,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期刊完全能够代替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但是我认为至少给我们期刊是留有空间的,我们现在二元化结构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事实上我认为这种二元化的结构,应该说对期刊的消费在下一步或者是在相当的时间内,我认为会呈上升的趋势,因为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期刊界里,现在北京悲观的论调比较多,但是我认为一个是我们的政策,一个是我们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我们的销售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期刊的内部管理。我认为管理的问题事实上还没有纳入我们,特别是媒体的管理没有真正地引起我们媒体界的高度重视,现在期刊业大家都是这样,谁的文章写得好就当主编,谁好像发了几本书就来当主编,主编没有这么好当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另外还有一个理性思考和人文思想是期刊的特性之一,这种特性之一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特别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我们的很多观念都需要改变,中国人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再想,作为我们人文的期刊,我们怎样来在这个时期寻找到我们期刊作为文化产品的特有的商业机会。
《商界》的情况我就简单地讲一讲,《商界》现在作为一种财经类期刊,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跟大家说,第一九千多本杂志单本期刊,广告收入我至少在中国期刊前五名,我是埋在水下的,媒体可以恐怖,无所谓,这第一个,另外发行量绝对是第一名,至于几十万,50万,60万,你们都认为我是胡说,谁也不相信,但是开源的调查,每年在全国的财经类发行我们都是第一名,后来又搞了一个低端读者,终端管理类,为其他的期刊,当然今天可能有很多在座的,我估计这个话说起来不是很好听,但是我认为从发行量来讲,我想跟大家讲个老实话,发行量远远地把第二名抛在后面,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期刊的空间,我们的广告收入从我们现在的估计,下一步应该在一定的时间内至少可以增加50%以上,没问题,因为这个需求量太大,我可以今天给大家讲,因为今天是圈内的人,我就说《商界》的广告有三个是在中国媒体界最牛的,第一广告回扣没有,广告公司代理点最多不超过三个点,你愿意干就干不干就拉倒,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这么大的广告量的回款率每年的回款率的损失不超过千分之一,我们所有的广告款不到不给你登,这些问题说明什么?内容为大,发行为大,发行量最大点,还有一个广告客户,广告公司有时候确实你跟他是一种驳议的过程,驳议的过程是慢慢养成习惯了,当然你自己做成强势的媒体才行,我们很多广告回扣、返点说实话已经被广告公司,4A公司说实话真的在压榨我们的利润,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作为《商界》来讲,打造《商界》的整体品牌,我们现在手里有七本杂志,我们在互联网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下一步还要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我们《商界》的目标,不想做一个期刊的集团公司,希望能够做一个媒体的集团公司,就是说各种影视、互联网、传统媒体,如果能够把它整个组成一个产业链,对未来的发展提升我们的品牌有很大的好处。
还有一个,我想讲最后一点,这个大题的最后一点,我们现在加强和龙源期刊网、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的长期合作,我认为对门户网站的合作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特别是这些年龙源给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推进。我今天看到数据非常地好,所以我觉得和龙源的合作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我想提一个建议,汤总、穆总,我们今后的合作,刚才张社长讲了,不是简单地把我的文章卖出去,我认为你们最好是能够跟我们的平台进行一种嫁接。《商界》,我的平台你怎么嫁接,现在一本杂志不是简单地卖一本杂志,我的活动,我的营销,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里边怎么来进行嫁接?下面可以探讨。
另外我想最后再讲一下,未来我们怎么样进行公司化、产品化。第一,我觉得改变观念,把期刊当做一个公司项目来经营,我们的杂志,我们的期刊社,说实话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事业单位,或者是上级拨款。我认为不管体制改不改,我跟我的下面很多人说,没有不好的杂志,只有不好的期刊主编,这个可能得罪很多人,那你来办这个杂志吧,如果这本杂志不好就改变你的定位,改变你的方向,把方向确定以后,主编就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
另外期刊的产品定位和商业模式是决定期刊发展的根本,这个我就不多阐述了。还有一个,多元化的推广自己的期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期刊,你们看在北京很多期刊,特别是我们财经类的期刊发行量,上万份的不多,但是人家活动做得好,咨询、活动、会展做得好,有点相当于咨询公司带期刊社这种性质,但是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广告也是一千多两千万,利润也很多,我认为就是说在未来,我们要打掉我们文人办刊的做法,我是文人,我办刊,社会应该很尊重我,没用,市场不相信我,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把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期刊的资源优势,寻找到更多的期刊的经济增长点,这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一个就是把互联网数字化,作为我们推广的重要渠道,最后我想谈加强期刊的服务性功能,我认为我们提供内容也是一种服务,但是现代社会的人已经对期刊远远不能满足这种,我们做商业财经很了解,给他提供很多类别,他需要很多很多的服务,这样把你的很多产业链延伸下来,我认为包括我们的科技产品,甚至是我们的文学刊物,都应该注意这些问题,我们的读者需要很多很多读物,我认为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变我们的角色意识,把传统的单一的需求改变为多方位的服务需求,以上就是我的一点感受,只是我这个人说话,因为今天都是同行,我觉得说得更加直接一点,大家可以交流,因为在我们明天办期刊这个职业当中,人家不是说要害一个朋友,就要让他办期刊。这两年我们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我们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是我们要长治久安,居安思危。谢谢大家! |